沙河那些平凡的人
五月一号,想记录一下在沙河遇到的平凡但却是在认真生活、诚实劳动的普通人。
卖水果的大叔
因着优购水果的价格高昂,各个私人的水果群就有了发展空间,在水果群里要上一份水果,等到下课叔叔阿姨送来就可以开吃。于是我就认识了众多小贩中的一个老板。
我倒是与他交流不多,零零散散了解到的信息大概就是老板是2010年沙河高教园修建起来六所大学开设分校区之后就开始在这边做生意了,学生需要水果,老板需要挣钱,于是大家皆大欢喜。我在有早市的时候一般不在水果群里买,或者可能去更远的郊区骑车路过采摘园顺便买点。在他这买水果呢,就得在东门等一位干瘦的中年男子骑着电动三轮拉来一箱水果,跟他说是哪群哪号买了啥,次数多了他也会记住你直接递给你。
老板在这做了十年的生意了,和学生们有了感情,做生意也很诚信,一天要给六个大学送四次水果,水果这么容易坏都几乎没很少出质量问题,即使是很忙,别人不满意的水果也能给换。

还有一次是我转发了一个患病的北航学长的水滴筹,学长刚本科毕业就患上了重病,叔叔看到了之后就问我,然后把水滴筹转发到了他经营的各个大学的水果群和同事的群里,这应该就是人间的对陌生人的善意,出于同感或是相似经历,都想着要帮一把。

玫瑰园的卖火烧的老板
在沙航的旁边的玫瑰园早市上,有卖各式各样的东西的人,水果啦,小吃啦,蔬菜啦总之就是农村集市上该有的都有,那时我大一,最喜欢的事就是周四周六没早八的早上起个大早骑着车去逛早市,买点嘎嘣脆的红富士,便宜到爆的柑橘,火龙果,买点胡辣汤和对夹,买点凉皮和卤煮,在早市上吃完回学校学习。
在胡辣汤对过的驴肉火烧的摊上,摊主是一对兄弟俩。摊上通常是红艳的剁好的驴肉,焦黄的烤好的火烧,绿色的剁好的香菜和辣椒,旁边再煮上一大锅羊汤,都冒着热腾腾的香气和热气。我往往是要一碗羊汤两个火烧,吃一口火烧满满一大口肉,再喝一口热乎的羊汤,略带着荤腥却又很香是北方的感觉。
我就是在那时候注意到了他。
他穿着油乎乎的围裙,脸上刚烧完柴火熏黑了,费力地把烙火烧的大锅架好后,用胳膊肘擦了擦汗呼出了一口气。他是老板的弟弟。老板这时候在忙着插好电源,他在后面搓着手局促地看着,想帮忙,伸出了手又缩了回去。
我愣住了。记忆里无数次相似的场景涌现了出来:在小学举行的元旦晚会上,帮别人搬好桌子却被骂了一顿,因为听错了他们的要求,然后被一脸嫌弃地说,“算了算了我来吧,这点事都干不好。”的我;在值日小组里我看到没干好的活想要帮忙却收回的手;后来无数次的这种场景我无助地局促地在旁边看着想要帮忙却生怕听错了别人的话反而帮倒忙的我……都在一瞬间和这一幕重合了。我意识到,他也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听障者。于是我特意上前,找他点餐,(是希望让他能帮上忙而不至于觉得不被需要),我指了指火烧,比出了二,又指了指羊汤,比出了一,他点点头,转过头指了一个后面的座位,我点点头,给他看了下我手机转账的记录。
坐在座位上,他送上来火烧和羊汤后,认真地擦桌子去了。我边吃边观察着他,他约莫四十岁,黢黑的脸上有很多道皱纹,干活的时候异常专注——这是自然的。我边吃着边想了很多,关于我自己和关于他人,关于他这四十年是怎么过来的,他过得好不好,关于我这二十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想了想,我遇到了很多善良的人,我也遇到了很多不理解的人,我有过痛苦与欢乐,我不希望别人也有这种痛苦,我决定为他做点什么,可是我悲哀地想到,我其实也做不了什么。
我吃完后,趁他们不忙的时候找到了他的哥哥也就是老板聊了起来:
“emmm,老板,我注意到他”,我指了一下他的弟弟,“他是听力不太好吗。”
老板边剁香菜边看了我一眼,空气中弥漫着香菜味,说:“奥他是我弟弟,他的确听力不太好,也说不了话。”
“咋整的啊。”
“嗨应该就是小时候发高烧烧坏的,大概是五六岁时候吧。”
我感到一种无力和绝望,想了解更多,却又不好太过直接戳中伤口,于是说:“你们老家是哪的啊,生意怎么样啊。”
“我和我弟弟是从河北来的,生意还行,就是来北京挣钱来了嘛,一天挣得挺多的,我弟弟也挺能干帮了我挺多,他不耳朵和嘴不好使嘛,我就带着他出来干,我们哥俩这么多年干的挺好的。”
我又聊了两句,最后说,“艾,那个其实我也是,听力不好,你看看我这,这么多年过得也挺不错的。”,他剁香菜的刀停了下来,抬头看了我一眼,我指了远处的北航校区,“我现在就在北航念书。”
老板来了客人,我没再打搅,我看着哥俩忙碌着,觉得能做的真的不多,我和他们唠嗑说那番话的意图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想让他们知道听力不好也没啥也照样能过得很好吧,但我又觉得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这点,能够很正常的谈论“耳朵和嘴不好使了”这些事并且在努力的活着。大约是不需要别人再多做什么了,除了社会保障残疾人证什么的,我能做的应该就是多多照顾生意多唠嗑,让他们去了解社会的政策,用我的心态多去影响别人。
我在他们的摊上徘徊了一会,骑车拎着我的水果回学校了,然后就是忙碌的期末考试。等我下个学期再去早市的时候才知道因为疫情防控这个早市已经停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兄弟二人。我担心着他们在这么大个北京城,人潮汹涌许多人来来去去,能否适应,有没有赚到钱,有没有过得好……
瓦罐饭的叔叔
沙东食堂一楼的瓦罐饭打饭的大叔每次都满满给你盛上一大勺,我喜欢吃那里的瓦罐红烧肉,不过我不吃肥肉每次总是把肥肉挑出来。来的次数多了,叔叔也就能记住了你,一来二去就能打上招呼,“叔,今天照样。”,“好嘞。”。“今天下课咋晚了呢?”,“嗨,今天老师拖堂了/和老师讨论了点东西。”
然后我了解到,大叔和上面那个卖水果的叔叔一样,也是沙河校区建起来就开始在这个窗口打饭了,这一打就是十年。十年来迎来了一批又一批,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瓦罐饭还是物美价廉的瓦罐饭,大叔却明显已经苍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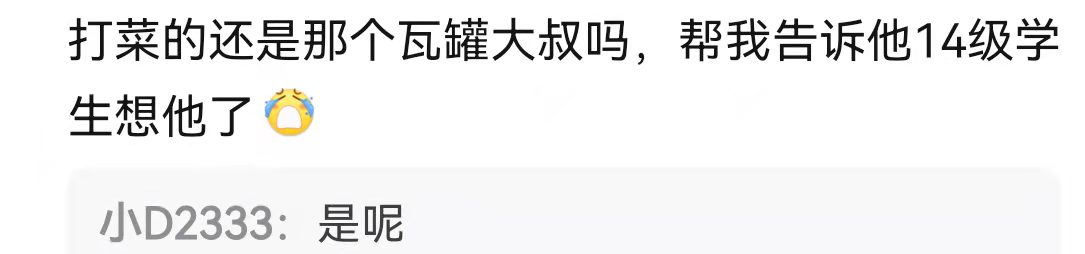
卖烤冷面手抓饼的叔叔
手抓饼群和水果群的性质一样,叔叔阿姨要早上起个大早准备好今天的材料,凉皮(只在4-10月有)、烤冷面、手抓饼,然后要为吃早饭的学生送去,午饭,晚饭都可以供应。凉皮是我在沙河吃到的唯一能入口的凉皮,我一般也会配上一份烤冷面,但我不太愿意吃他家的手抓饼。
阿姨应该是负责做,叔叔是负责送,我们从来没见过阿姨,但是每次都能在东门看到叔叔骑着电动车从外交学院过来。摘下大头盔,微胖的脸上露出和蔼的笑容,然后珍重地把打包袋递给你,一日三次日日皆然风雨无阻,久而久之下雨刮风的日子里我们也不忍心让他们再送就会少要。
日子照常的过着,忽然有一天,叔叔告诉我们一个噩耗,阿姨的妈妈去世了不得不回老家,暂时不能为我们做煎饼了。我们安慰叔叔阿姨,让他们节哀。这一去就是一个多月,然后叔叔告诉我们他们那边有了疫情,高速封路,回不了北京了,盼啊盼终于清零了,等他们疫情稳定就回北京,然而正好五一期间北京戒严了,,,我们很担心叔叔阿姨的平安,也担心几个月没有做生意,生活是否还好。




